想要有本羅智成的詩集~
藍色時期
──那些難以啟齒的憂傷
沒有堂皇的喟嘆可以置換:
我仍在熱戀
自覺幼稚
卻即將老去
V
在時光的出海口
所有記憶都被風化
只有遺憾
像感覺的化石
裸露在乾涸的河床
VI
觸撫角獸的頭骨
閱讀殘損的詩行
可以窺見當時的
原野與年輕的
夢境嗎
所有遺憾
原本都有
甜美的來歷
XIV
什麼是不變的呢?
一切記憶與書寫
不過是刻舟求劍:
我們把事件的記憶
深鏤船舷
流動的河水卻在原處
改變了事件
我曾經愛過她
或那樣地懊喪過嗎?
被書寫的我和
書寫現場的我
在這首詩的
行進當中
便迅速分離出
無數個念頭的
距離
XX
但是她並不放棄
隔著髮絲與淚水吻我
好像屬於我們的文明明晨就消失
又好像我們總是為
尚未降臨的幸福與憂傷
忘情地幸福與憂傷
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
Thought-provoking
Bennett’s words:
Future past tense
To translate well, you need to know the
culture as well.
Death is the world behind the door. You
thought the door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who knows what’s behind it.
Be young, be flexible. Don’t be dominated
by America.
Finding an ideal job is like finding your
true love. You need to date a lot to marry one. So does a perfect job!
Comment:
A person
with strong opinions, straight forward, and is not afraid to speak ill of
others. Must has his wits.
Seldom do I have time to sit in front of my laptop, wondering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recently. I have always been busy. Busy with debate,
consciousness paper, hanging out with Jason, Constance, Anne, …… My sophomore
life has been so concentrated on certain things that it amazed me when I thought
of it. It’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 have such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certain friends. I’m not kidding, really. I have always been afraid of over-interacting
with others. There is no so called BFF in my dictionary since I have never stuck
to any friendship for so long. I hate the idea of being restricted in a group.
So I kept the distance from others. Same as I got bored with others easily, I was
afraid that my friends found me tedious as well. And the best way to avoid the
embarrassment and the waste of time is to not spend too much time together.
However, I miraculously spent so much time with you guys. J always
challenges my ideas and argues with me for trifles. I wish he could open more
of his heart to me though, or I felt I kinda bump into walls whenever I chat
with him. C is talented and determined, but she is also cute and kind to laugh
heartedly for my horrible jokes. She has the magic power to make every seemly
impossible things become likely. We should’ve try to finish our project! A is
obviously most close to me since we almost see each other every day. I don’t
know how I am going to get used to the days without seeing her so often.
French
Debate (English!)
Chinese Flute
Consciousness paper
Sometimes I wonder why I always squeeze my time so much. Why can’t I
lead a simple life, savoring literature and arts?
你問我為什麼要上咖啡館
太喜歡這篇文章了說出了我對咖啡館的感受很多時候無非就是在都市的夾縫中求取一個屬於自我的空間我們只剩下咖啡館《只剩下咖啡館,只剩下星期一》文: 楊照 1998/02/拾穗月刊 我知道數以十計的咖啡館,在台北。可是我沒有打算寫導遊導覽,介紹你們去這些咖啡館。 我知道一家冷氣永遠開得太強的咖啡館。裡面服務的小姐,自己都戲稱那個地方是寒帶。坐在那裡,總是可以比別人早一點察覺到要變天下雨了。外頭空氣中的濕度一升高,咖啡館面街的大片玻璃就開始結霧,水珠凝得夠大,到了有足以淌流的重量,雨就落下來了。履試不爽。 我還知道一家燈光永遠太暗的咖啡館。灰黑的四壁及天花板都保留了最純粹的水泥原色,未作任何裝飾,純粹到也不掛任何的照明工具。只有每張小桌上一盞十燭光左右的燈泡,甚至不足以照亮檯燈本身的燈座,乍看之下像是一隻隻漂浮在空中的螢火蟲,異常堅持地寸步不肯飛離開。我曾在那螢弱的光線下讀完李敖的回憶錄,若干瞬間錯覺以為自己置身在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都有的潮寒土牢裡。 我知道許多家總是味道濃重的咖啡館。煙味咖啡味混著某種雨季的霉意,一層疊一層沾黏桌布和椅墊,以及一切紡織纖維上,把那些細微的空隙填補的滿滿的。甚至不需經年累月,那種味道裡只有膚淺的歲月感,沒有時間滄桑的。在努力維持簇新外表的咖啡館裡,就是會有那種不肯隨著店門開關而新陳代謝的嗅覺刺激,像是舊式擦髮油的浮華紳士,昨夜殘留在枕頭上的味道。 我還知道更多家音樂永遠不對勁的咖啡館。最主要是不用心,看待音樂的態度就是「有了就好」。標準就是一張「李察.克萊德蒙」矇混到底。要不然就是那種翻唱英文老式情歌,連原本最情緒化,最悲愴的小提琴聲音,在裡面都不客氣的擺出虛情假意的敷衍姿態。更不要提歌聲了。要不然就是逼你聽一次又一次,最近唱片行賣得最熱門的CD。聽一百次張惠妹。再聽一百次許茹芸。然後是鄭中基梁詠琪……從這館聽到那館。 還有一種不用心是拿音樂嚇你。干擾你的情緒。永遠猜不出來下一秒。下一分鐘,會冒出什麼東西來。巴哈的雙小提琴協奏曲最後一個音符還繞在門柱間,就突然發現後面追來了用誇張美聲唱法的「雨夜花」。至於Bill Evans的爵士鋼琴,就被搭配了安室奈美惠蹦蹦跳跳的「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Celebrate? 」還有還有,南美風的新世紀音樂會毫不客氣的被接上一段金戈鐵馬。風疾雨遽,琵琶演奏的「十面埋伏」。這些,都不是我的想像,是真真實實發生過的咖啡館傳奇。 我知道一批批風格彼此抄襲的咖啡館。我知道有好幾家總是有人講話講得像在吵架的咖啡館。我知道一堆咖啡作假的咖啡館,他們的卡布其諾只是用普通綜合咖啡加上鮮奶油。巧克力粉和彩色糖粒。我知道另外一堆簡餐做得極其馬虎的咖啡館 …… 這些我都知道。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寫導遊導覽了。 有時候看見人家興味盎然地把臺北的咖啡館介紹的多彩多姿,還附上光澤適恰的照片,我都不免有些納悶。這些人,排除掉做廣告不算,這些人真的常常去到咖啡館裡嗎? 還是這些人都具有比我更堅毅強韌十倍百倍的都市性格? 對我而言,咖啡館是臺北貧乏文化中的不得已,永遠成不了光榮驕傲。是因為我們失去了太多東西,找不到太多以前本來屬於我們或者將來應該屬於我們的地方,所以輾轉流落咖啡館。 咖啡館於是成了一種欠缺的提醒,走進咖啡館而想起來我們倒底少了什麼;走進咖啡館於是成了一種荒涼憂鬱的經驗,因為我們沒有勇氣沒有能力去追尋建造那真正欠缺的,所以到咖啡館去,至少不要遺忘掉欠缺的感覺。 只剩下咖啡館了。在咖啡館想著我們失去了家,失去了可以長久待著也不會膩煩的家的感覺,失去了在家裡可以不受打擾的城堡式安全戒心,也失去了能夠在家裡坐著躺著悠閒的完整時間。 在咖啡館想著我們失去了朋友,那種可以互相賴在彼此家裡的沙發上,不小心就因酒或午后涼風而沈沈睡去的朋友,以及朋友的家。我們也失去了看一個好朋友不知不覺在講話中安穩睡去的沈靜寬容。 還想著我們失去了山林和海洋。山林。海洋當然還是都在的,是我們失去了與他們的日常聯絡管道。山林,海洋,甚至陽光與雲,變成我們生活的某些額外的東西,不在編制裡,也不在「正常」的意義運作裡繼續影響我們。 只剩下星期一,只剩下咖啡館。 還想著我們沒有的人文傳統。一個在咖啡館裡讀詩、討論哲學、爭辯政治立場的人文傳統。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還遺留在文明的彼岸。詩只存在於極少數高中生的課本或筆記簿的邊緣塗鴉裡;哲學在學院裡艱苦流傳,而且缺乏創新討論,至於政治立場,計程車上的爭辯遠比咖啡館裡的普遍。激烈而且嚴肅。 在那個我們沒有移植進來的人文傳統裡,咖啡館和酒館一樣,讓人暴白自己。向自己或他人誠實暴白自己。咖啡館和酒館是孿生的一對場所,酒使人醉,咖啡逼人清醒,在最醉與最清醒的兩極情境裡,存在著剝除了含混面具之後的赤裸裸。血淋淋自我。 在那個人文傳統裡,許多基礎的結構都是二元搭配的。聖潔與世俗,理智與感情,精神與物質。於是而有咖啡館與酒館。 我們沒有那個傳統,只剩下咖啡館。就像香港人在都市化發展中,因為居住越來越擁擠,人在鴿子籠般的屋子裡越來越待不住。有一段時間他們只擁有茶樓,只剩下茶樓。不過咖啡館比茶樓至少多了一點空間,多了一點孤獨,相對的,也就容 許了多一點嘈雜中的誠實。 一九九六年中以後,有一段時間,我過的日子最接近典型的臺北人。有一份全職上班的工作,在民生東路的大樓裡分配到一間約莫三坪大的辦公室。換句話說,生活裡有了一個不斷引誘我逃離的,別人指定的中心。 逃到哪裡去? 逃到哪裡去才能不要看起來像別人希望看到的國際事務部主任?逃到哪裡去才不需要接無窮又無聊的電話,對著原本不認識或不屑認識的政客們解釋一些他們應該知道卻又偷懶不去學習的事? 逃到哪裡去才能碰到真心,才能對還好奇想聽真話的人,說些不掩飾、不心虛的真話? 逃到哪裡去才能整理自己的怯懦、恐懼、挫敗、憤恨,以及洶湧而來的愛怨情仇? 只剩下咖啡館了。尤其是星期一,早上開完「主管會報」之後,我就格外想逃。一種沒有未來,沒有明天式的逃離衝動。覺得自己就要活不過這最最憂鬱,最最死氣,最後的星期一。 於是,每個焦躁不安的星期一,我造訪那些太冷、太暗、太吵、太臭、太假的臺北咖啡館。在咖啡館裡撿拾自我,尋找真心。並且,努力寫出星期二就要見報的副刊專欄稿。 於是,在「星期一咖啡館」裡寫出來的這些稿子,有了一種我以前的作品裡不曾有的末世焦躁,絕望掙扎(desperation) 的印記。我在想像的「星期一咖啡館」裡啜飲著焦味苦口的咖啡,招來所有識與不識的朋友或敵人們,強迫他們聽我陳述彷彿再不說就會把我噎死的種種感受。 在只剩下星期一,只剩下咖啡館。時間與空間雙重的逼迫下,我利用文字,勉強的追覓那些應該存在卻不存在的東西。家、個人城堡、朋友、山林、海洋、人文傳統、詩、哲學、關於政治社會與公理正義的爭辯,以及最重要的,真心與愛情。 我努力地用文字在這個貧乏的時代,開張這樣一家「星期一咖啡館」,販賣這些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的一點香澀氣味。 (完) (聯合文學之「Cafe' Monday」)
2013年11月20日 星期三
不妥又怎樣

知道聶永真一陣子了,卻沒讀過他的文字。沒想到昨天卻看到王郁仁買了他的雜文集”不妥”,小巧的口袋書硬包裝,有質感而不過度精緻。
莫名其妙的就被我先拿來看了。
我始終不明白那些被寫在散文集裡的,非常真實的日常生活、感情世界,那些被書寫的對象,他們都不會覺得自己的行為被攤在陽光下嗎? 我也不知道作家對於公開自己的腦袋這件事情可以多開放? 很多時候,我不知道如何隱藏、包裝自己的文字而寧肯不公開,因為我是隻自閉的小蝸牛,不想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的蝸牛殼下藏了什麼,即使根本就沒有幾個人想看,也沒有幾個人看完還記得。
我也很想知道散文集裡呈現的作家,跟實際的人到底落差有多少,聶永真是不是真的像他的文字那樣有點自以為雅痞,會不耐的翻白眼,穿窄管褲戴粗框眼鏡,對於愛情跟理想冷嘲熱諷居多。到底文字傳達了多少真實? 如果我見到聶永真本人,我會說什麼? 我覺得他的文字有個性但我不特別偏好,他的人應該有趣但我們應該合不來。他會覺得我太迂腐感性天真,我會覺得他做作自以為是,就像我跟那些只會打招呼的人,即使偶遇也就停留在偶遇,不會有進一步的交集。
我可以不愛他的文字,但是依然有被撞擊的時候。因為那是同為都市觀察者,同為龐大工業體系份子的產生的理解,日常生活中種種不被察覺的荒謬,還有我們對於生命最終還是一個人的體認。我像是經歷一場有所感觸的對話,可能不見得愉快,但是至少有片段是值得記憶的。
這段文字讓我想到Celine Dion的 All by myself
雖然歌詞意境跟文章不太搭
“片段中有些散落,有些深刻……”張懸的歌詞突然浮現腦海,這就是讀散文的好處,像是走在秋天的小徑上,落英繽紛,而我拾起某片形狀特殊的葉片,不為什麼,剛好貼近我內心的空缺。很平常,很隨意,我可能每天上下學都經過,卻不曾意識到。
但是因為我讀了雜文集,戴上聶永真那副跩跩的黑框眼鏡,我可以告訴你,其實就只是這麼單純,阿不然你想怎樣?
P.S 忽然覺得自己講話變得像王郁仁了。過度口語化的文字好像不太好? 但是寫起來很爽讀起來很有力。
2013年11月5日 星期二
寂寞貴族--窮得只剩下錢跟自負
是島國子民太過安逸,還是香港太過擁擠喧鬧,我在行走的每一刻,都恨不得離開這座金錢堆疊的繁華,窮人的呻吟蓋在腳下,依稀聽聞。
這裡不重視環保,資源回收沒人要做,反正只要有錢,沒有什麼買不到。每座地鐵站之上幾乎都有商場,甚至是終點站柴灣。什麼時候我們需要不斷的消費呢?
這裡的建築直入雲霄,是現代通天塔嗎?當人類越靠近雲端,越忘了腳下的芸芸眾生,還在每天的生存中掙扎。
我記得那一點也不氣派的維多利亞港,銅鑼灣海邊一角,小船搖搖,比高雄碼頭還破落。我都要懷疑自己是在這個國際轉運點嗎?但是香港的確存在著這樣的地方。銅鑼灣有精品林立的大街,也有庶民穿梭的小路。即使是大都會,常民生活如昔。
我看見那些沒有活力的中學生,是因為清晨早起嗎?他們的白裙還有些皺褶,臉上還充滿了夜讀的痕跡。我的中學時代,也是這般迷迷糊糊的模樣嗎?
但是我也看到香港大學的學生是如何有自信,如何敢表達,除了流利的英文,他們對事情的了解、分析,並不是我在台大常見的。我還記得他們如何拐彎抹角的嘲笑警察,這些學法律的菁英們,戲謔的嘴角,有一種熟悉世故的弧度。
我不知道我如果真的在這裡生活,是會變得堅強無情,還是會被擊垮,落慌而逃? 但我能做的也只有好好的珍惜台北,同時好好的準備自己,因為不是每個地方都像寶島一樣可愛。
不只大自然使人謙卑,龐大的城市也讓人渺小,因為我們無可避免地被資本主義吞噬、宰制,無法自外於這體系。我渴望有一天到紐約、巴黎、倫敦等大城好好的感受大城市的氣派蓬勃,但我清楚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因為我的心底,永遠都會有這麼一座小小的城,小小的島。
我從未如此想念台北,想念台南、宜蘭、台東,甚至是醜不拉機毫無特色的桃園,原來淨土是這麼一回事。
生命裡到底最後會剩下什麼呢?故鄉,異地,究竟什麼會留在心中?我覺得香港予我一種巨大的虛無感,彷彿我的靈魂最終會被那龐大的金錢黑洞吞噬。當我不比別人有錢,當我不比別人優秀,我彷彿就失去了人的價值。
但我於一個毫不留戀的城市,遇見一群我想記住的人。
跟逸瀟的深夜聊天、清晨散步,都讓我敬佩這個有想法、有行動力的中國女孩;表情超多、超萌的日本大叔Toshi還有也很可愛的評審Jesus;可敬的對手Kasif,真希望有機會多聊聊;HKUEDT 的Anthony, Cat, Mashiat, Vincent 還有其他人,以及最可愛的Hyewon
and Daniel。
我還記得冠軍賽是如何震撼我,為什麼有人可以不帶紙筆辯論,還能條理分明地反駁對方,Kip, Daryl, Andrea……,這些人真的太可怕了。辯論真的如侯門,一入深似海,一下海就難脫身了,因為你會渴望自己能成為那樣的人,在台上自信、從容的解構對方。
我需要好好地調整自己學辯論的方式。
20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TJ晃蕩日記2—筆墨山林
繼上回沿河濱公園騎車到大稻埕之後,今天老天再度賞臉,秋光正好,讓每周三都像是小周末,任我們去探險。
之前在台北村落之聲上看到關於蟾蜍山的城市散步旅行,加上意識報學長曾經誤闖軍事基地而被審問的趣聞,都讓我很好奇這個學校後山的小聚落。即使比賽、期中考在即,我還是需要一個悠閒的周三下午,讓我跟J去晃蕩。畢竟生活是一把琴,時緊時鬆,才能奏出悠揚,我們都不是不知疲倦的機器人。
綠藤攀附紅磚屋,藍色大門兀自明亮,有誰看的見裡面?
不像文章裡敘述的,好似寶藏巖那般,我眼見的煥民新村安靜的彷彿無人居住,偶然腳步聲驚動了狗兒,少被打擾的牠們抗議許久,讓我們也走得有些遲疑。我本來以為會看到一些海報阿旗幟的,但是什麼都沒有,整座山靜悄悄的。
走在登山步道上,青苔跟雜草遍生,甚至草叢、樹木都枝椏都要佔據路面了,我們幾乎寸步難行,必須要穿過重重尖刺。(好笑的是,我毫髮無傷,J卻被劃了個口子XD) 但我們膽戰心驚的穿越後,卻發現此路不通==
於是我們只好折返,又不死心的試著從其他小路登頂,卻都無功而返。J剛好瞥見老房裡的一位伯伯正在洗碗,就請教了一下。原來現在路都被封住了,根本上不去。(是怕升斗小民誤闖雷達站?該不會是學長的誤闖給他們的教訓?) 而且也不知道何時要拆遷,伯伯乾瘦的身子顯得單薄,伴隨著不時的用力吸氣,我聽了有點心疼。同為山城,寶藏巖轉型為藝術村,煥民新村卻感覺凋敝不堪,秋日午後的陽光灑落,只有貓狗有膽放肆,極少居民在走動,彷彿時空都凝滯。
不知道為什麼,來台北念書一年了,不深不淺的跑過一些地方,也就一年,就有許多地方消失了,華光、紹興等等,煥民新村應該很快也會消失了吧!我忽然覺得又感傷又憤怒,為什麼這個政府一天到晚都在拆窮人的房子,為什麼都不會拆那些影響山區、海岸線的建築?也是只是突如其來的情緒,卻讓我在寫這篇日記的當下,萌生了在意識報寫篇文章介紹這個地方的念頭,至少我可以用筆記錄這個地方,一個被遺忘的角落,不能任由記憶雜草叢生,就此湮沒。
原來遺世而獨立是這樣,超出於時間之外。人車喧嘩的馬路旁,彎進小巷,他這麼默默存在著。走著走著,我們都要忘記自己是在台北市,最繁華的首都阿!
探險因為路被封死了而只好中止,還剩下大把大把的時間跟陽光,我們就騎往信義區。沿著芳蘭路直行,隨意的拐了彎,就發現”福州山公園”的招牌。雖然是個迷你公園,階梯的坡度卻也夠我這隻飼料雞氣喘吁吁了(J倒是一派輕鬆,大氣不喘一下)瞭望台視野極好,信義區一覽無遺。此時的風極舒服,吹走我們的燥熱,卻又不刺骨。然後我們又接著走到富陽公園,所謂的溼地也不過只是一畦小水塘,不免失望。”台北人這麼容易滿足啊!” 從小在台中長大的J忍不住奚落,但在寸土寸金的都市,每一方綠意都得來不易,而我選擇知足,讓我們在直入雲霄的101旁,有這麼一座小丘陵,一個公園,讓我可以走點路不用吸廢氣,爬個坡假裝自己在原始林中。
超級迷你的富陽公園
下山之後,J帶我去一家奇妙的文具行。我們倆玩色鉛筆玩了好久,不停在筆記本上塗抹,這種混和的筆芯可以畫出豐富的色彩,也許這就是我嚮往的一支筆,充滿變化。
從山林到筆墨,TJ又度過一個有趣的下午,兩個喜歡遊手好閒的傢伙,不知道下次又會騎著腳踏車,閒逛到何處?
【我們的島】搶救蟾蜍山聚落 http://pnn.pts.org.tw/main/2013/09/30/%E3%80%90%E6%88%91%E5%80%91%E7%9A%84%E5%B3%B6%E3%80%91%E6%90%B6%E6%95%91%E8%9F%BE%E8%9C%8D%E5%B1%B1%E8%81%9A%E8%90%BD/
台北村落之聲: 你所不知道的公館──蟾蜍山 http://www.urstaipei.net/citywalker/walk?view=adm_new&id=265
Café’ Jam 好像不開了,偶爾不定時才會開店,下次有空再去碰碰運氣。https://www.facebook.com/HappyPartyLabo/info?ref=stream
2013年10月14日 星期一
柯裕棻:把生活中的沙礫打磨成珍珠
讀完浮生草,有好多喜歡的段落,還沒有時間慢慢打字,先貼一些找到的訪談跟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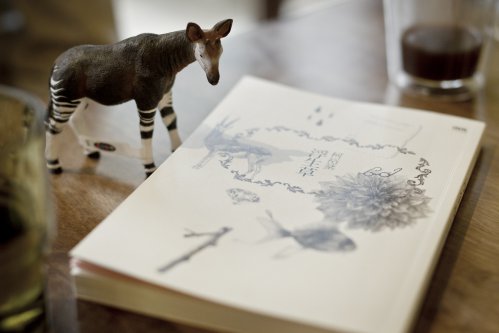
【集散地】日常瑣碎轉化成的珠玉淨光——柯裕棻《洪荒三疊》
當文字成了「作品」,「作家」的身分就格外需要意識,隨之浮出的,是讀者的存在。「不能說是『很在意讀者』,而是說,讀者的想像終究是存在的。完全沒有在乎讀者的寫作是很危險的。」但事實上,到底要給讀者什麼,是無法設計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到底有沒有把文字的重量,與我要講的感覺完整寫出來?」
這樣近乎優柔寡斷般的修寫回望,不煩膩嗎?「只要是散文,某種程度上都是愉快的。即使一再一再地修改,也都是愉快的。」她說。「當然會有一氣呵成寫完的篇章,但是完全不需要改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她不輕不重地下了這四個字。
〔散文.快問快答〕
Q1. 您自己在散文寫作時,對真實與虛構的態度是?
柯裕棻:每一個作家寫的東西,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是出於自己的腦子。小說似乎允許完全的捏造,但事實上,小說洩漏的作者本身,比散文更多。小說是完全無法假裝成另外一個人的。小說裡每一個角色、每一個為之生、為之死的信念,你認為什麼是愛恨、什麼是失落、什麼是道義,都是出於自己。小說是最能洩漏這些的。
散文可以剪裁,可以轉換。雖然還是無法憑空捏造,但我可以讓它摸不著邊際,因為我不需要讓它經過「一個事件」;小說不行,即使是科幻小說,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所有的細節與邏輯,都要能夠說服讀者,不管怎樣,都不可能沒有洩露自己。
不管寫散文或是寫小說,都還是同一個我。散文也是真真假假,你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只是不那麼真。真實與虛假的灰色地帶是很大的,因為或多或少都做了處理。有誰寫散文不處理的呢?
Q2. 看過印象最深刻、至今記憶猶新的一篇散文是?
柯裕棻:張愛玲的〈華麗緣〉。我每隔一陣子都會拿出來重讀。它裡面並沒有特別寫什麼,既沒有任何道德訴求,也沒有任何啟發或道理,只是講去看戲這件事,寫完就寫完了。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打動我,也許裡頭終究還是有一個無法戳出來的什麼,或是藏得非常非常裡面,不像張愛玲其他篇章動不動就要浮出來直接感嘆蒼涼,卻怎麼讀怎麼揪心。
Q3. 您最喜歡的散文作家是?
柯裕棻:木心。木心的作品是我的床頭書,他的詩或散文都很厲害,讀起來像是一般的白話文,但通篇讀完會覺得「為什麼我心底會有這種感覺呢?」他的文字魔法不是單在一兩句話上,有時候你想特別引用還真抓不出來,那好厲害。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但我相信那絕對不是直覺寫出來的,一定是反覆修剪。而木心的功力就在於:你根本看不出他修剪過,簡直是「無刀之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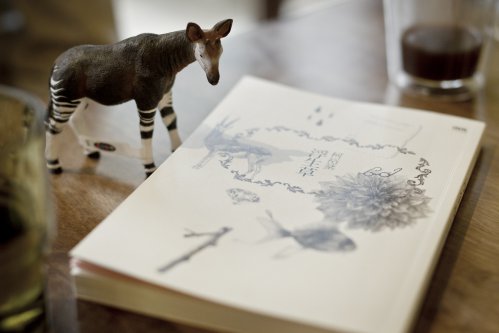
【集散地】日常瑣碎轉化成的珠玉淨光——柯裕棻《洪荒三疊》
當文字成了「作品」,「作家」的身分就格外需要意識,隨之浮出的,是讀者的存在。「不能說是『很在意讀者』,而是說,讀者的想像終究是存在的。完全沒有在乎讀者的寫作是很危險的。」但事實上,到底要給讀者什麼,是無法設計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到底有沒有把文字的重量,與我要講的感覺完整寫出來?」
這樣近乎優柔寡斷般的修寫回望,不煩膩嗎?「只要是散文,某種程度上都是愉快的。即使一再一再地修改,也都是愉快的。」她說。「當然會有一氣呵成寫完的篇章,但是完全不需要改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她不輕不重地下了這四個字。
〔散文.快問快答〕
Q1. 您自己在散文寫作時,對真實與虛構的態度是?
柯裕棻:每一個作家寫的東西,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是出於自己的腦子。小說似乎允許完全的捏造,但事實上,小說洩漏的作者本身,比散文更多。小說是完全無法假裝成另外一個人的。小說裡每一個角色、每一個為之生、為之死的信念,你認為什麼是愛恨、什麼是失落、什麼是道義,都是出於自己。小說是最能洩漏這些的。
散文可以剪裁,可以轉換。雖然還是無法憑空捏造,但我可以讓它摸不著邊際,因為我不需要讓它經過「一個事件」;小說不行,即使是科幻小說,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所有的細節與邏輯,都要能夠說服讀者,不管怎樣,都不可能沒有洩露自己。
不管寫散文或是寫小說,都還是同一個我。散文也是真真假假,你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只是不那麼真。真實與虛假的灰色地帶是很大的,因為或多或少都做了處理。有誰寫散文不處理的呢?
Q2. 看過印象最深刻、至今記憶猶新的一篇散文是?
柯裕棻:張愛玲的〈華麗緣〉。我每隔一陣子都會拿出來重讀。它裡面並沒有特別寫什麼,既沒有任何道德訴求,也沒有任何啟發或道理,只是講去看戲這件事,寫完就寫完了。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打動我,也許裡頭終究還是有一個無法戳出來的什麼,或是藏得非常非常裡面,不像張愛玲其他篇章動不動就要浮出來直接感嘆蒼涼,卻怎麼讀怎麼揪心。
Q3. 您最喜歡的散文作家是?
柯裕棻:木心。木心的作品是我的床頭書,他的詩或散文都很厲害,讀起來像是一般的白話文,但通篇讀完會覺得「為什麼我心底會有這種感覺呢?」他的文字魔法不是單在一兩句話上,有時候你想特別引用還真抓不出來,那好厲害。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但我相信那絕對不是直覺寫出來的,一定是反覆修剪。而木心的功力就在於:你根本看不出他修剪過,簡直是「無刀之刀」。

浮生草:序(節錄)
人間一渡
入夏之後,胡亂忙了一陣,等我能夠靜下來整理這本散文時,蟬鳴已不再喧騰,中元節將近,街巷都飄著香燭紙錢的煙氣。這是夏日尾聲的氣息,過了這個彼岸之節,喘口氣,人們就開始準備中秋了。
中元之後我到山上去,正午的山寺濃蔭寂然擁簇,靜謐又炎熱,日子亙古悠長,像青空下一聲孤單的蟬鳴。看這些稿子就想起寫它們的時候,彷彿才是昨天的事,親近得像髮茨緩緩沁下的汗水,那麼濡貼,怎麼,怎麼轉眼都成雲煙。
這些是近三四年來寫的文章,一部份是簡單的日常觀察,一部份是讀書寫作之事。儘管看來似乎截然不同,但它們確實是同一種生活,有些甚至是在同一天之內寫下的所見所思。
我看見自己尖銳的棱角收斂了,叛逆的羽翼彷彿剪除了。我百般不願意地,逐步將自己放手交給世事人情,日日在頹喪放棄與執拗不馴的矛盾中拉扯,終於被拋磨成一個看似圓融平靜的人了。
但是在這些文字的另一面,我仍然看見心裡軟陷的,偏執幽暗的那些,像熔岩一樣灼燙難以平息卻默默含著的意念。它們毫無保留地展現在關於讀書寫作的文章裡。我不確定是否我太無情,以致這些年的紛擾仍然無法動搖或改變我絲毫,或是我太冷淡所以不輕易釋放甚麼。我執拗如昔,只是終究學會了將苦惱、厭倦和熱情一起蓄放在心裡,不動聲色地活著。奇怪,以前竟然覺得這很難。
這幾年日子看似平靜,但也起起伏伏經過一些激流和漩渦,幸而都安穩渡過了。有些事已不堪聞問,亦有不值一哂的,當然也有一想起來就高興或惱火的,簡單的喜怒。我常常覺得不論再怎麼安穩,若是一不小心有個閃失,就全盤皆輸了。人世是這樣的,方寸之下,就是地獄了(在中元節之後想這個,也實在太應景)。因此每見世間飲食男女山川興廢,眾女子妍媸各異,更覺幽美不可名狀。
書中關於日常生活與女子瑣事的文字,是從這樣的體悟而來。
一般而言,讀書寫作等事是文人的前台表演,而生活瑣事則為後台微不足觀的背景。但我怎麼看都覺得,寫日常瑣事的那些其實是生活的表層文字,他們工整而冷靜;有關讀書寫作的這些則非常熱切,是表層文字。這些更貼近自我,更往內心深掘,它們其實非常私密。我以為我不輕易將心剜出,寫的當時我一點也不擔憂,如今湊在一起看,就有一覽無遺的危險了。
希望讀者也能如此理解這些文章,並且包容我又想太多了。
農曆七月的氣氛總是恐懼中帶著刺激,甚至是壓抑的歡欣。這個月我們時時提醒自己,需尊敬不可知,需與可怖的它者共存,需低首斂眉謹慎行事,真心明白生命渺小無常。這是人鬼同途相互依傍的日子,人間此渡,誰的心裡都藏著一隻陰鬼。
此刻安坐著心平氣和翻看稿子,一切看似理所當然。可是仔細想想,這些時而冷靜時而熱切的文字真是難得——實在沒有比晴日靜好時回看彼時風雨更的心平氣和的了。
2013年10月9日 星期三
For the sake of CONNECTION
He left
Internet for a year just like now how I dread to go on Facebook, knowing how
much time I am going to waste on it.
And he
was back, after a year of offline life.
He
realized that he couldn’t live without Internet because it is where people are.
No matter how slightly known or how far people are apart, at least they are
connec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I admire
his courage to experiment an offline life, not to mention that he’s actually a
tech-writer. But I still think things c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had he spent
his year differently. Just now, I could think of so many ways to spend my year
without Internet nagging me.
A year
in Amazon, Sahara, North Pole, Tibet or anywhere, where I don’t need Internet
to survive.
But what’s
next?
I still
need to come back. Without Internet, how am I going to tell my stories to others?
How am I going to keep in touch with my friends?
I see
the point of this article. It’s nearly impossible to live offline in a modern
world, if you want to keep pace with it, unless you exile yourself to remote
places where Internet is a luxury instead of necessity. Because writing a
physical letter is simply too official or too troublesome. Because calling
someone you don’t really know is a hundred times embarrassing than sending a
Facebook message, and you might don’t have the person’s number at all.
So I will
keep living online. Love and hate the Internet at the same time. Since we desire so much to be heard, to be connected, as if we are branches of a tree and the Internet supplies water to sustain our lives. And maybe take
some time off to escape this horrible lover once in a while to cure my
addiction to him.
Excerpt:
1. It's hard to say exactly what changed. I guess those first months felt so good because I felt the absence of the pressures of the internet. My freedom felt tangible. But when I stopped seeing my life in the context of "I don't use the internet," the offline existence became mundane, and the worst sides of myself began to emerge.
2. But then I spoke with Nathan Jurgenson, a ‘net theorist who helped organize the conference.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s a lot of "reality" in the virtual, and a lot of "virtual" in our reality. When we use a phone or a computer we're still flesh-and-blood humans, occupying time and space. When we're frolicking through a field somewhere, our gadgets stowed far away, the internet still impacts our thinking: "Will I tweet about this when I get back?"
3. My plan was to leave the internet and therefore find the "real" Paul and get in touch with the "real" world, but the real Paul and the real world are already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internet. Not to say that my life wasn't different without the internet, just that it wasn't real life.
I'd read enough blog posts and magazine articles and books about how the internet makes us lonely, or stupid, or lonely and stupid, that I'd begun to believe them. I wanted to figure out what the internet was "doing to me," so I could fight back. But the internet isn't an individual pursuit, it's something we do with each other. The internet is where people are.
When I return to the internet, I might not use it well. I might waste time, or get distracted, or click on all the wrong links. I won't have as much time to read or introspect or write the great American sci-fi novel.
But at least I'll be connected.
2013年10月7日 星期一
Onora O'Neill: What we don't understand about trust
It’s not about how much trust we have for
others and the society. It’s about trusting the people who are trustworthy and
make ourselves trustworthy.
1. It's judging how trustworthy people are in particular respects. Intelligently placed and intelligently refused trust is the proper aim.
2. Put trustworthiness before trust. Trust is the response.Trustworthiness is what we have to judge.
3. Trust, in the end, is distinctive because it's given by other people. If you make yourself vulnerable to the other party,then that is very good evidence that you are trustworthy and you have confidence in what you are saying.
南風輕拂,卻是死亡的氣息
《南風》鐘聖雄 X 許震唐 專訪,住在毀滅性建設下的台灣人民
摘錄
"有一群住在台灣「母親之河」出海口的人,百年來過著耕種、捕魚的平淡生活。他們的祖先曾經說,這裡有田可種做,有海可漁獲,絕對不愁沒東西吃。
然而,自從十幾年前他們村子南邊蓋了世界第一的巨大石化工廠後,一切都變了。他們的西瓜只開花卻不結果。他們的農作產量逐年下滑。他們的海裡漸漸補不到魚。他們熟悉的河口不再有野鳥下蛋,甜美的文蛤也變得酸苦。甚至,就連他們的身體也變得像土地、海洋一樣,逐漸失去了生命力。這裡是彰化縣大城鄉,全彰化縣罹癌率最高的地方。
當南風吹撫,雨水如淚落下,母親的臂彎成了彼此枯寂的墳墓。這些橫跨了二十年的影像記錄,要告訴我們的訊息除了生,也有死;還有,南風來的時候他們如何活。"
"我希望我的影像可以像子彈一樣,在當下去促成改變,而不是像禮砲,只能在事後去榮耀自己或他人。我希望我的照片,永遠都可以在當下發揮作用。"
"如果所謂的發展勢必要有人犧牲,那這個發展就一定有問題,它是犧牲式的發展。我今天拍這個東西不只是要談特定的污染,而是整體發展思維的反省。我們到底踩著什麼樣的人在發展?誰被發展了?誰又被犧牲了?這種毀滅式的發展是不是沒有替代方案?"
"對我而言,環境污染從來就是一個階級問題。"
2013年10月5日 星期六
我們夢想的台北市
雖然不知道他的背景或是能力,但是蠻認同他對城市的理念,不知道之後會有什麼更具體的政策?(一個不是台北長大,在台北念書,很關心台北的人XD)
顧立雄:偉大的城市要有河、故事及幸福
一個偉大的城市要有3個條件,第一,像倫敦、紐約等大城市,都要有一條河,在兼顧防洪下,讓人可以親近每條河流;第二,要有故事,找尋台北特有的故事,結合空間、在地社區與人文,創造活化、細緻,讓人驚豔;第三,這個城市的處處,都要展現他的進步與幸福。例如最近郝龍斌要求台北市最後一班的公車一定要準點,就是貼心而友善的想法。這種小確幸要能持續去做。
會不會擔心因此被批評,他則說,「人活到55歲,如果過去一張白紙,完全沒有被攻擊的地方,那也不是很奇怪嗎?」
顧立雄:偉大的城市要有河、故事及幸福
一個偉大的城市要有3個條件,第一,像倫敦、紐約等大城市,都要有一條河,在兼顧防洪下,讓人可以親近每條河流;第二,要有故事,找尋台北特有的故事,結合空間、在地社區與人文,創造活化、細緻,讓人驚豔;第三,這個城市的處處,都要展現他的進步與幸福。例如最近郝龍斌要求台北市最後一班的公車一定要準點,就是貼心而友善的想法。這種小確幸要能持續去做。
會不會擔心因此被批評,他則說,「人活到55歲,如果過去一張白紙,完全沒有被攻擊的地方,那也不是很奇怪嗎?」
2013年9月28日 星期六
Respect Existence, or Expect Resistence
Overwhelmed. Absolutely overwhelmed.
Hardly can an article about protesting can be in such a depth with vivid description and touching stories. There are so many parts strike chords with me that I just have to cut and share them.
周三下午剛走過一場在椰林大道的遊行
烈日下
汗水流淌著我們的青春驕傲
每個步伐都是我們對政治的失望跟關切
而這個故事是在遙遠的土耳其
場景迥異 讀來卻備感熟悉:
他們只是站著 沉默地凝視
而你還要說他們是暴民?
他們拿起書本 閱讀是最好的抗爭姿態
因為思想就是最強大的武器
希望你可以花點時間 讀完它
因為這是一篇非常用心的文章
更因為裡面充滿令人動容的故事
然後 或許你會明白 抗爭是什麼
埃爾多安的一席話,完全證明了他腦袋裡頭的民主等同於非常狹義的多數決,同時也明白的揭示了他就是一個擁選票而自重的威權主義者。這位自認為「民主」卻假裝沒有「憲政」、不知對話與協商為何物、甚至連裝蒜一下都不會的總理先生,接下來幾天的言論也同樣驚人。他先是在隔天面對記者訪問的時候表示,自己「不會在執行我的計畫時,還要徵詢塔克辛廣場上那些無賴的同意」,然後又非常白目的選在這個時候悠哉自得的出訪北非,完全不把抗議聲浪當一回事。埃爾多安的例子表露出一個高度自我中心的政府領導人如何看待權力與政治,無怪六月上旬《經濟學人》的封面故事會把他比作極權時代的土耳其蘇丹。其實,這位備受爭議的土耳其政治家,在早年的政治生涯裡面,就曾談過他對民主的看法。「民主就像是一列火車,」他說道:「你搭上它,往目的地出發,等到站的時候,也就是該下車的時候了。」
而當抗議群眾重新回到這座耗盡力氣從政府手中搶回來的小公園時,他們開始自發性地做起了掃除工作。聽起來好像很尋常的一件事情,對吧?可是你可以想像:一個清早還在街頭跟警察混戰的土耳其人,這會兒竟然拿著掃把跟畚箕在清理戰場,還把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幾個小時前剛從政府手中扔向他們的催淚瓦斯罐給撿起來,看了看,或許苦笑一下,然後丟進垃圾堆裡頭去──這畫面,我覺得更像是一部電影。
「佔領」雖然意味著把生活奉獻給抗爭,但抗爭當然不是生活的全部。同樣的道理,格茲公園裡頭的幾萬民眾,自也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之道。當抗議群眾回到公園、建立起一座迷你的「帳篷之城」以後,許多自發性的組織與活動,也就跟著冒出來了。前述的大掃除,自然是建立起共同生活空間的第一步。接下來,一批醫療專業人員很快地在公園裡頭建立起醫務站,另一些人則負責管理各地送來的食物、飲水等物資。有人弄到了發電機,搞定了許多需要用電的場合,額外還架設了一座手機充電站。另外,廣場與公園周遭原本大門深鎖的店家,這會兒也開始支援起抗議群眾的衛生需要,其中甚至還包括了一間星巴克(考慮到這個資本主義的壞蛋象徵越來越常被各種抗議活動拿出來針對,這個景象其實還挺奇妙的= =")。
6月11日的激戰過後,留在廣場上的抗議者累得身心俱疲,再度遭到強烈打擊,他們的挫敗與憤懣不難想見。然而,12日這天,忽然有個叫Davide Martello的德國音樂家,默默地帶著幾個人,把一架鋼琴給拖到了塔克辛廣場的入口處。隔晚,他在廣場上幾不間斷地為群眾彈奏了十四個小時。很奇妙的,塔克辛廣場上人們的情緒就這麼跟著和緩、平靜了下來,許多多人圍著這架鋼琴聆聽了整夜的演奏會,偶爾跟著唱起了歌,或者為一首曲子的尾聲喝采,廣場上的一些警察,甚至還跑過來向他致意。
我們常常會讀到一個詞叫作「國家機器」,這個詞原先其實帶有一點負面意涵,意指政府體制只是一具為實現統治目的而運作的大型機器,而並不以人為它的核心考量。與此相應的,6月下旬的《經濟學人》,也有一篇文章把埃爾多安的多數決主義喻為「殭屍民主」,意思是說:這樣的民主圖具形式,卻「heartless」,並不能真正實現制度「為人民服務」的原初目的。「國家機器」與「殭屍民主」,說的其實都是同樣一個道理。國家和民主,最初都是為了給人們更好的生活而被創造出來的。但是,當國家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機器,當民主變成了對群眾聲音毫無感知的殭屍,它們還有存在的意義嗎?「閱讀抗議」凸顯了政府對各種各樣的人,他們的理性、情感、故事、聲音全然的漠視,這是一個需要學習尊重人的存在的政府。廣場上的人讀著凱末爾的傳記與演講錄,讀馬奎茲,讀卡夫卡,他們在這個失去靈魂的政府面前展示了有關於人的各種書寫,集體靜默卻聲勢懾人。而毫不意外的,許多人手中都捧著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一個關於孤獨的個人,如何在極權體制底下掙扎求存的故事。
http://timeandimage.pixnet.net/blog/post/183721337/1
Hardly can an article about protesting can be in such a depth with vivid description and touching stories. There are so many parts strike chords with me that I just have to cut and share them.
周三下午剛走過一場在椰林大道的遊行
烈日下
汗水流淌著我們的青春驕傲
每個步伐都是我們對政治的失望跟關切
而這個故事是在遙遠的土耳其
場景迥異 讀來卻備感熟悉:
他們只是站著 沉默地凝視
而你還要說他們是暴民?
他們拿起書本 閱讀是最好的抗爭姿態
因為思想就是最強大的武器
希望你可以花點時間 讀完它
因為這是一篇非常用心的文章
更因為裡面充滿令人動容的故事
然後 或許你會明白 抗爭是什麼
以下是我摘錄的一些感人小片段
而當抗議群眾重新回到這座耗盡力氣從政府手中搶回來的小公園時,他們開始自發性地做起了掃除工作。聽起來好像很尋常的一件事情,對吧?可是你可以想像:一個清早還在街頭跟警察混戰的土耳其人,這會兒竟然拿著掃把跟畚箕在清理戰場,還把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幾個小時前剛從政府手中扔向他們的催淚瓦斯罐給撿起來,看了看,或許苦笑一下,然後丟進垃圾堆裡頭去──這畫面,我覺得更像是一部電影。
「佔領」雖然意味著把生活奉獻給抗爭,但抗爭當然不是生活的全部。同樣的道理,格茲公園裡頭的幾萬民眾,自也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之道。當抗議群眾回到公園、建立起一座迷你的「帳篷之城」以後,許多自發性的組織與活動,也就跟著冒出來了。前述的大掃除,自然是建立起共同生活空間的第一步。接下來,一批醫療專業人員很快地在公園裡頭建立起醫務站,另一些人則負責管理各地送來的食物、飲水等物資。有人弄到了發電機,搞定了許多需要用電的場合,額外還架設了一座手機充電站。另外,廣場與公園周遭原本大門深鎖的店家,這會兒也開始支援起抗議群眾的衛生需要,其中甚至還包括了一間星巴克(考慮到這個資本主義的壞蛋象徵越來越常被各種抗議活動拿出來針對,這個景象其實還挺奇妙的= =")。
6月11日的激戰過後,留在廣場上的抗議者累得身心俱疲,再度遭到強烈打擊,他們的挫敗與憤懣不難想見。然而,12日這天,忽然有個叫Davide Martello的德國音樂家,默默地帶著幾個人,把一架鋼琴給拖到了塔克辛廣場的入口處。隔晚,他在廣場上幾不間斷地為群眾彈奏了十四個小時。很奇妙的,塔克辛廣場上人們的情緒就這麼跟著和緩、平靜了下來,許多多人圍著這架鋼琴聆聽了整夜的演奏會,偶爾跟著唱起了歌,或者為一首曲子的尾聲喝采,廣場上的一些警察,甚至還跑過來向他致意。
我們常常會讀到一個詞叫作「國家機器」,這個詞原先其實帶有一點負面意涵,意指政府體制只是一具為實現統治目的而運作的大型機器,而並不以人為它的核心考量。與此相應的,6月下旬的《經濟學人》,也有一篇文章把埃爾多安的多數決主義喻為「殭屍民主」,意思是說:這樣的民主圖具形式,卻「heartless」,並不能真正實現制度「為人民服務」的原初目的。「國家機器」與「殭屍民主」,說的其實都是同樣一個道理。國家和民主,最初都是為了給人們更好的生活而被創造出來的。但是,當國家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機器,當民主變成了對群眾聲音毫無感知的殭屍,它們還有存在的意義嗎?「閱讀抗議」凸顯了政府對各種各樣的人,他們的理性、情感、故事、聲音全然的漠視,這是一個需要學習尊重人的存在的政府。廣場上的人讀著凱末爾的傳記與演講錄,讀馬奎茲,讀卡夫卡,他們在這個失去靈魂的政府面前展示了有關於人的各種書寫,集體靜默卻聲勢懾人。而毫不意外的,許多人手中都捧著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一個關於孤獨的個人,如何在極權體制底下掙扎求存的故事。
http://timeandimage.pixnet.net/blog/post/183721337/1
2013年9月18日 星期三
I will remember to smile next time
Dear Anne,
Since you see us
as a sweet couple, I will use this metaphor to explain what I want to say.
(Actually, being partners is also like in a relationship because you have
commitments and expectations to each other.) Being a couple is really not an
easy job. You have to constantly remind yourself why you like the person in the
first place, especially after the honeymoon. (Hey, isn’t this summer like our
honeymoon XD) But we often forget to do so, or at least I do.
After saying
goodbye to you, my heart suddenly sank. I felt so weird. We didn’t have a fight
or any misunderstanding. But I didn’t see a smile on your face when I said
goodbye. Maybe you are just exhausted. But it is not the facial expression that
I saw, but the heart. And suddenly, I miss your smile so much.
Every time I nagged
you, I would ask myself, “Am I right to be so demanding?” Like I said, I am a
perfectionist. So I want everything to be on schedule. I want to start
discussing or debating at 6 p.m. sharp. I want to meet people on time. I hate
when things become out of control. But truth is, they always do. And then I will
feel unhappy. I will stop trying hard. However, things shouldn’t be like this.
(Why am I using so many “like”? Hmm, it must be that I am writing to you!)
When I focus so
much on competition, I tend to forget the fun of debate. (It’s not that HKDO
doesn’t worth us working our ass out!) But I don’t like myself being so harsh.
It should be fun! I still remember what Won Chian lim said, debate is about
having fun. Though I couldn’t believe that I actually quoted him, but he is
right. Damn right! And I should always bear that in mind. Or you can remind me
when I become too obsessive.
So why am I writing
you a long and weak-structured letter in English? Well, at first, I just wanted
to send you a song, which we sang a lot together. You will always be my dearest
Anne, a good friend and a great partner. I will still be picky about your
grammar mistakes and I will still want to occupy your time to practice as much
as possible. But I want us both being happy during the process. It’s lovely to
sing and play with you, and I want to make this upcoming month as lovely and memorable
as it can be, no matter how many things are nagging us. So smile and go!
Let’s sing it
next time! You know that I see your true color.
Always yours,
Tammy
Tammy
True Color
You with the sad eyes
Don't be discouraged
Oh I realize
It’s hard to take courage
In a world full of people
You can lose sight of it all
And the darkness inside you
Can make you feel so small
But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re beautiful,
Like a rainbow
Show me a smile then,
Don't be unhappy, can't remember
When I last saw you laughing
If this world makes you crazy
And you've taken all you can bear
You call me up
Because you know I'll be there
And I'll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re beautiful,
Like a rainbow
(When I last saw you laughing)
If this world makes you crazy
And you've taken all you can bear
You call me up
Because you know I'll be there
And I'll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re beautiful,
Like a rainbow
You with the sad eyes
Don't be discouraged
Oh I realize
It’s hard to take courage
In a world full of people
You can lose sight of it all
And the darkness inside you
Can make you feel so small
But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re beautiful,
Like a rainbow
Show me a smile then,
Don't be unhappy, can't remember
When I last saw you laughing
If this world makes you crazy
And you've taken all you can bear
You call me up
Because you know I'll be there
And I'll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re beautiful,
Like a rainbow
(When I last saw you laughing)
If this world makes you crazy
And you've taken all you can bear
You call me up
Because you know I'll be there
And I'll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re beautiful,
Like a rainbow
2013年9月11日 星期三
旅行就該走自己的路
旅行就是走自己的路,不必在意別人的眼光,不必這麼害怕跟別人相同。
“你不能把整座城市變成一座博物館。” 你無法不提起此處曾經發生過的戰爭,但你不能停在這裡。如果你找到一個極端,將會使過去變的廉價;但若走到另一個極端,將會使現在受到限制。你必須讓這個地方成長,使它成為當地人民──以及遊客──的家園。活著,不是只為了記得。
在府城晃蕩了四天,不斷地思索保存老屋跟開發之間的平衡。保存過去的重要性究竟多大?值得我們如此費心?當過去的生活型態跟樣貌徹底消失,我們又承受了什麼樣的損失?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過去,都有各自的歷史包衭,如何不忘記歷史,又如何積極向前看,是身為城市居民的我們,應當要思索的。像是老屋再生,如何避免文化資本被簡化成經濟資本,讓人只識情調,不解歷史脈絡?
道格在柏林體驗了其掙扎於自身定位的不協調感,但我讀陳思宏的"叛逆柏林",卻又是一個任文青撒野的好所在,當真是一座城市百種感受。
瑞士這個中立國,遠離衝突雖讓她享有平靜,卻也讓他缺乏歷史感。
別再費盡心思拍出好照片。這跟軍鈞之前提到的概念很像,與其執著於拍出可以在臉書上炫耀的圖片,不如讓自己全然地享受每一個當下。照片再美,比得過明信片嗎?更何況,網路發達的世代,flickr上遍地即是。我可以理解這樣的觀點,但我並不全然同意。我還是希望自己懂得攝影,起碼從鏡頭看去的世界是不一樣的,而或許拿著鏡頭時,會對周圍的環境更有覺察力。總之,只要謹記一個原則,把握當下,不管是否拿著相機,都要記得讓自己拋開束縛的去體驗,以自己是否能好好感受為最優先考量。
旅行市場的成長公式:
中產階級的擴張+流行文化的影響+旅行容易度的提升=大量的旅遊人潮
"在現代,一場離家幾千里的旅程,都是從建立一個部落格開始的──近幾年來,這幾乎已成為一種義務。"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只是我覺得現代人是如此害怕被遺忘,因此幾乎什麼事都急著要分享,彷彿不這麼做就會被淹沒在無數個臉書帳好中。只是當我們亟欲呈現自己給別人看時,那個是真正的"自我"嗎?還是那必定是我們修飾包裝過的形象,甚至我們自己都深信不疑。
道格對於書寫的型態提出了細緻的觀察:"當年我母親寫信時,也有事物會令她分心,不過這些事物不在信紙上,而在周圍的環境中:車流、鳥鳴、人影、氣味,它們就屬於那裏。這些事物不會將他抽離,反而能令她更融入周遭環境。這就是寫信跟寫電子郵件的關鍵差異──除了螢幕,我們和其他事物沒有連結。"不知道為什麼,使用電子產品時,我們全神貫注的程度往往讓我們徹底跟周圍環境脫節。但是寫信時卻不太會,是因為電腦的使用跟書寫對大腦的刺激不同嗎?我還記得每次寫信時,筆到之處,都充滿了那個地方的氣味,甚至是我的味道、或是極度感性之下的眼淚等等,但是電子郵件不會記錄這些,他連筆跡都統一,讀信的人也無法從字跡判斷我當時的心情。無奈人都是懶惰的,許久沒有拿筆寫字,還是貪圖方便,就如同正在打字的我。
道格精闢的下了結論:時至今日,"寄自iPhone"已成為我們這個年代的專屬郵戳。
最重要的旅行應用程式就是"關機"。
我們都忘了如何過無聊、什麼都不做的日子,都忘了不用電腦,該如何把日子填滿。我們不能忍受未知,不能接受不舒適的環境,但是道格說了,旅行就是享受一個過程,從什麼都不太懂,逐漸摸清方向,融入當地的生活。不然,如果一切都在清楚掌握中,你就錯過了任何可能的驚喜了。
我不禁慶幸這次環島,我跟西瓜做到了放空自己。我們可以在一片草地待上一天,可以在一間飄著咖啡香的書店窩上一個下午。旅行就不應該有既定的時間表,逼著自己去完成。
第一眼看威尼斯,應該在破曉時。
最道德的旅遊路線就是往人多的地方走。這些地方有太多遊客,他們知道要如何處理訪客。(真的嗎?)開發新路線,反而可能破壞生態。(我覺得那是指野外,城市中的巷弄應該還不至於如此。)
如今人人立志成為旅人,對"觀光客"這個名詞則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兩者之間的界線到底是什麼?
旅客是主動的,努力探索人事物、勇於冒險跟體驗。
觀光客是被動的:他期望有趣的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他只是去"觀光"。
看似旅人比起觀光客要來的好,但是作者持平的評論道,其實被動的旅行也有其需要,對許多工作過度的人而言,想要利用假期放鬆有什麼錯?不過,我想觀光客之所以惹人厭,就在於他們找樂子時忽略了當地的文化傳統跟習俗,變成了常民生活的入侵者。或許身為觀光客,就應當識大體的到度假村、遊樂園之類的地方,享受明確的服務。
但作者又說,如果是以心態區分的話,那目的地是哪根本無關緊要。你可以是迪士尼樂園中的旅人,也可以是西藏的觀光客。
最終,去哪裡旅行並不重要,而是你如何展開你的旅程。真正指引你的,不是規則跟數字,而是永不滿足的好奇心。
道格以一個平凡的上班族身分告訴我們,即使你沒有勇氣挑戰那些無人前往的私房秘境,即使你想走的路線其實是大部分觀光客的必經之路,那又如何?旅行在這個年代已經變得太過強調獨特性,大家都害怕去熱門景點,好像這樣就太平庸了。但我們卻忘記,熱門景點之所以為熱門景點,就在於它的好歷久不衰。
下一次出走前,我該回來看看這篇讀書筆記!
訂閱:
意見 (Atom)









